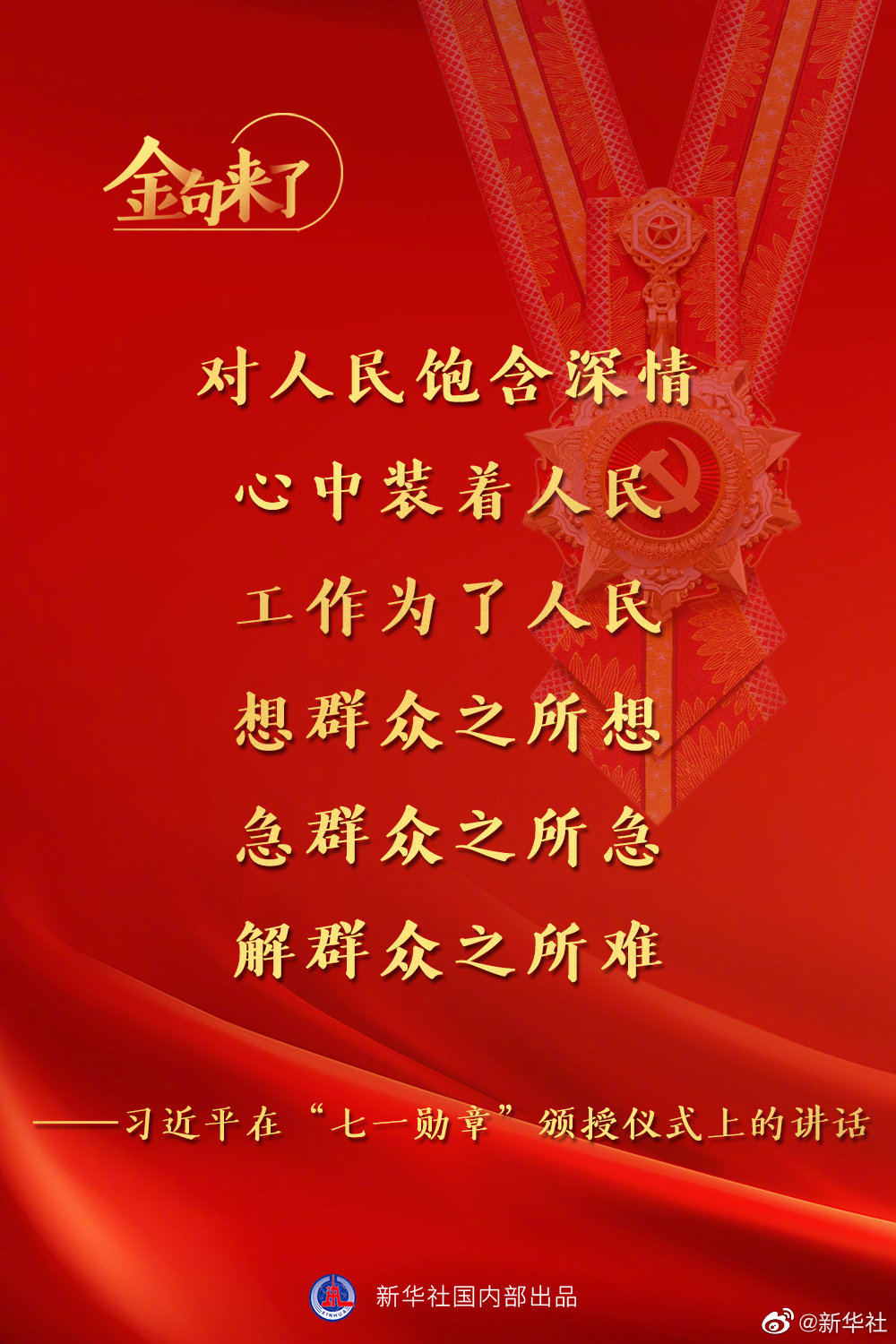湖南就业创业网
把记忆的灰尘都抖落在画布,黄亮的“岁月静好”源于自愈
黄亮这次在站台dRoom空间展出的作品,大部分灰灰的,青绿青绿的,像在角落被遗忘多年的旧物,让人忍不住想要在画前轻轻吹一口气,也想掸掸上面的灰尘。他重复着一些主题,比如空白信件、手作的宗教法器、手部、贝壳河蚌,粗粝的麻布上没有任何松节油的气味,完全是干干的厚重的颜料堆积形成的哑光质感。人叫黄亮,可能因为生活在东北,下笔却显得寂寥、清冷又萧瑟。展览名字《岁月静好》是在看完整个展览后才觉得真是恰如其分,回味时觉得它们无一例外都是真诚的、耐看的、安静又有渗透力,慢慢内心也被默默关照治愈。
刚刚进入展厅,又听说了艺术家年轻时候被误诊的经历,顿时感受到画面中的孤寂是如此诚恳,希望他年轻时候可以快乐一点就好了。第一个区域中,黄亮重复画着女人肢体的局部,某种微妙的眼神,看书的手,摆弄植物的手,颜料太干以至于画面像是即将剥落但仍然无人问津的墙面。他略显拘谨老气地描绘这些生活中或者不真实的细节和场景,用看不到笔触的技法柔和地呈现这些散发着淡淡哀伤的美丽女性。艺术家极其吝啬地使用明快色彩与另外一种画家创作时会使用的爆发力,画面就像无声默片,直指内心的孤独和长久以来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
黄亮说“绘画由内而外地固化所珍藏的情感和时光的细节,只要情感有驱动,我的绘画就停不下来。”没错啊,驱动他的正是心中无法说清的闷闷的情感。像是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的字里行间中流露的孤寂感,不是过分难过,也不是惊天动地的悲伤。可能“哀而不伤”正是一种中国古人的美学智慧,如今似乎被逐渐抛弃,但被黄亮一直留着。
黄亮画贝壳和河蚌,因为那一方小小的空间就可以把内心呵护看顾,获得一些短暂的安全感。黄亮画桌子上的静物,但不是莫兰迪的那种圣洁而极致的形式感,而是完全个人主义的心情日记。这些斑驳的情绪被反复的描绘这么多年,同时也能感受到他又想要克制、简洁、精准一些,所以画面中的张力是平衡又玄妙,很好回味。
后来,我觉得这些画面其实是艺术家的情绪出口,把孤独画出去了,人才会通畅些。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情绪找出口,当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恰巧拥有宣泄的出口,但艺术家无疑幸运的拥有创造力并将能心中的情绪由画笔输出、排解、释然。居住在作品中的归属感,我无法体会,但有点明白为什么展览名字叫“岁月静好”,因为这些平面才是他的舒适区。
上一篇:周恩来总理的诗歌情怀